一個華僑家庭的遭遇
傅國存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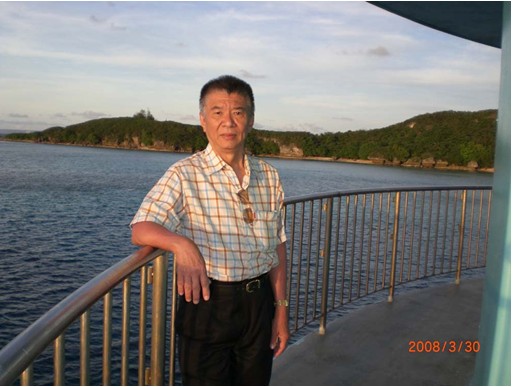
筆者傅國存

筆者伉儷在美國與女兒、女婿及外孫度天倫之樂
本人及家族簡況
我是印尼蘇島棉蘭歸僑,1953年棉華中學初中畢業後回國. 在北京上學, 六十五中高中畢業,因品學兼優, 1956年獲保送北京俄語學院留蘇預備部學習, 準備於1957年公派蘇聯留學,因當時中蘇關係破裂,出國不成. 當年秋天,轉送清華大學冶金系學習, 1962年春畢業, 分配到一機部農機研究所,從事科研工作, 1970年下放湖南常德幹校務農, 1973年調回北京. 1974年申請出國到香港, 1976年移居澳門至今. 期間曾在港澳貿易公司任職,穿梭港澳間,跑國內貿易,也常出差東南亞, 蹲點搞生意. 1999年返回澳門,被聘為澳門潮州同鄉會秘書, 二十一世紀初退休. 2008年當選澳門歸僑總會理事兼副秘書長, 主編 “澳門僑訊’ , 因患重症辭職養病在家。
我們家族是由先祖父被賣“豬仔”出洋始移民印尼的。先祖父在種植園合約期滿後,在民禮埠做裁縫小生意立腳. 先父傅石生,印尼出生,曾在上海暨大肄業,精通中、英、印尼文和中國多種方言. 多年在外國船務公司任職文書,行船跑碼頭,數月才返家一次,勞苦奔波. 待遇尚可,是小康之家,但因要負擔我們八兄妹糊口供書,外加我二叔英年辭世,撫養二嬸和一堂兄的重擔也由先父挑起,還有一位小叔和奶奶,食指浩繁,因此家境也不算富裕。
先父的愛國情懷
先父是民盟蘇島支部的骨幹成員之一,又是“蘇門答腊民報”主要負責人之一,在棉蘭也算得上是鐡杆“紅卡撐”(閩南語,即擁護中國共產黨,從事棉華社會的愛國民主運動人士)。我當時年幼,所知不多, 只知道當時家裡經常賓客盈門,有許多叔叔阿姨前來家座談開會。這些人後來都成為棉蘭華僑總會的骨幹份子, 知名的僑領. 家裡還常有“不速之客”留宿,有的還逗留頗久,深居簡出,後來才知是先父掩護的被迫害和通緝的中共或馬共黨員。此外,先父和當時流落到印尼、新加坡、香港的中共黨員、革命者、文化人如連貫、胡愈之、夏 衍、王任叔、邵宗漢、費振東, 饒彰風等等,都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。
家父的愛國情懷,僅從我們八兄妹的起名便略可知曉。我們這一輩,按家譜應是昌字輩,但家父一反傳統,全部改為國字輩,所起名字都反映了國家各個時期的興衰。以我為例,生於1937年11月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後,故取名國存(希望國家不被外族滅亡,千秋長存);最小的妹妹生於1949年5月,故取名國紅(紅色中國即將誕生)。到了下一輩,則按“詩”字輩家譜命名,先父健在時,孫輩多請他老人家起名,小女出世時,正值國內大搞「比、學、趕、幫、超」運動,故爺爺給她起名詩超(即“超英趕美”之意),也就是說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,先父的愛國情懷依然不變。
早於1948年,先父就把大哥送往香港學習,後返回大陸參加革命,加入東江遊擊隊,從事文藝宣傳工作,轉業後留廣州工作;次年又把二哥送回國,他立即參加了革命部隊,加入共產黨,參加過解放戰爭,爾後,他又赴朝參戰,負傷回國,復原後, 先後在北京“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”和新疆伊黎地區黨委機關工作; 1952,1953年,三哥、我和堂兄也相繼回國升學.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,六弟也回國深造. 也就是說,我們家八兄妹,有五個在先父的鼓勵支持下,回國學習,建設祖國. 五弟有病,七弟八妹年紀尚小,留在印尼,六七十年代後,國內形勢風雲突變,他們再沒有步我們的後塵。
家族的不幸遭遇
這樣一個愛國的家庭,下場卻是不幸和悲涼。
第一波衝擊是反右運動. 最老實且平時沈默寡言的大哥,不知如何得罪了單位領導,被打成“右派”,降級減薪,還蹲過勞改農場,已過適婚年齡的他,對象離棄,至終身孤寡,一生被毀掉了.二哥因單位領導用極其惡毒的語言辱罵先父,他氣憤不過,與對方爭執,亦被打成“右派”.曾坐牢及被送往勞改場勞改.一兒一女四口之家,生活拮据, 只能靠先母的私蓄和親友的接濟過日子, 甚至賣家當賣血維生。
曾當過“右派”的大哥和二哥,文革中更不能幸免,吃盡苦頭,自不必說. 大哥和二哥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才得以出境到香港, 後來二哥又移民加拿大。
第二波是文化大革命,1966年五弟因罹患淋巴癌,在印尼醫治無效,因在京的兄嫂是醫生或護士,很自然就想到往北京求醫. 那時正是紅衛兵當道,醫院留醫的病人,凡非「紅五類」,不予治理. 當時我三哥任職的北京醫學院附屬醫院的領導明確跟我三哥講,不歡迎海外來的病人,也不讓他與五弟接觸. 作為兄嫂的我們,如坐針毯,惶惶不可終日. 五弟已病入膏肓,癌症已轉移到全身,包括脊椎骨,後果堪虞. 國內兄弟想要陪伴出境,簡直是天方夜談. 無奈之下,我們兄弟只好含淚做出痛苦的決定,讓他孤身上路,唯有祈求上蒼保佑, 所幸五弟吉人天相,終能平安回到家中. 半年後,終被頑疾奪去了他年輕的生命。
再說三哥,反右時雖未被打成“右派”,但文革時因曾提過想護送五弟出境,被污衊為「有叛逃思想」,給戴上“右傾”帽子, 全家被下放到甘肅偏遠小山溝. 1973年才得以出境香港,後轉澳門鏡湖醫院工作. 當時還處文革末期,國內局勢不明朗,不免心有餘悸. 在親友的協助下,跑到泰國謀生,轉行當紡織機器修理工。
在文革中,我響應號召,積極投入,善意向領導提出批評和意見,因文筆尚可,切中要害,被當權者視為眼中釘、“黑筆桿”,因華僑性格使然,平時喜歡交朋結友,在家中暢談及招待膳食,結果被扣上「裴多菲俱樂部」組織者及“5
1976年先父回國內旅遊探親,六弟和先父團聚,因此卻被廣西某工廠領導懷疑六弟為特嫌,送縣公安局立案審查. 先父曾為國家和共產黨出過力的愛國華僑, 竟如此款待, 情何以堪?怎叫人不傷心絕頂?!
更加使我們感到椎心之痛的是,先父熱愛祖國,性格執著,對共產黨深信不疑,對大哥和二哥不理解,一直以來認為兒子不對,使他無面目見人,長時間生活在失望和茫然之中,因此和大哥、二哥反目成仇,不相往來, 直至鬱鬱而終. 一個大好的家庭就這樣被毀掉了. 當局對我們兄弟的批鬥審查,毫無根據,最後當然是不能成立. 把人摧殘至此,竟以『事出有因,查無實據』,草草開個平反會,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。
不是我們耿耿於懷,對過去的問題抓住不放, 問題在於當局沒有做好善後工作,因此受害者的心靈創傷未能撫平. 現在的二哥,心靈的創傷仍未癒,心灰意冷, 因為他的原單位,一句賠理道歉的話都沒有. 他引以為傲的赴朝參戰、負傷復原時發的榮譽軍人證書也在文革中被抄走,至今不獲發還,幾十年被克扣工資和剝奪勞動權利也沒有得到補償. 前些時他兒子親自跑了一趟新彊,想為他追回這些東西, 討個說法,卻不得要領。
對民族國家的熱愛堅貞不移
我們家族的那段遭遇,在歸國華僑群中,只是冰山一角. 但我們和廣大僑胞一樣,雖然遭遇不公和不幸,仍秉承先輩的愛國情懷,對民族對國家之熱愛堅貞不移. 我們現在雖然是異地愛國,但對民族和祖國的關注有增無減. 國父
當年,我們遭遇不公和不幸時,曾經有過怨恨:「我愛祖國,祖國卻不愛我」. 後來細想不對,祖國是所有炎黃子孫的共同家園,人人有份,她沒有理由不愛我們,個別人不能代表祖國. 有愧的是,當時太幼稚,愛國帶有愚昧性,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,明知有些施政是荒謬絕倫的,卻不敢提出異議,更不用說反抗了. 吃一塹,長一智,現在我們的愛國質量提高了,再不盲從了. 從辯證唯物論的觀點看,世界上絕無永遠光榮正確的人和事,我們應持的態度是:對的支持和擁護,好的讚;錯的反對和抵制,狠批判. 這才是負責任的真正愛國者。
幾十年都過去了,這些往事絕少向外人提及. 原因之一,是怕引起博同情的誤解;原因之二, 是先父的愛國情懷是廣大華僑的共性,沒有大書的必要,怕引起顯耀之嫌; 原因之三,是寫出這段經歷,免不了要帶出一些人和事,有些先父的知交,時任國家的高官要職,又怕有攀附權貴,謀取利益或一官半職之嫌,因為要遵循先父的嚴訓:『為國效力,是單向閥,不圖回報』,因此不敢造次. 現在我已屆耄耋之年,又罹患癌症頑疾,何野心之有?但說無妨了。




